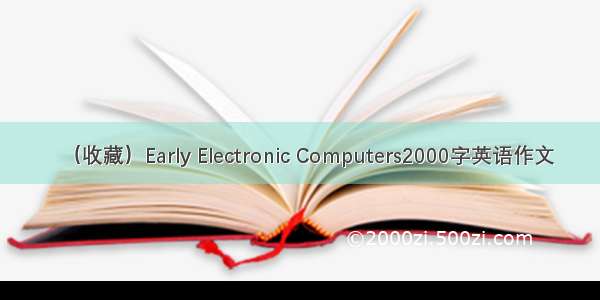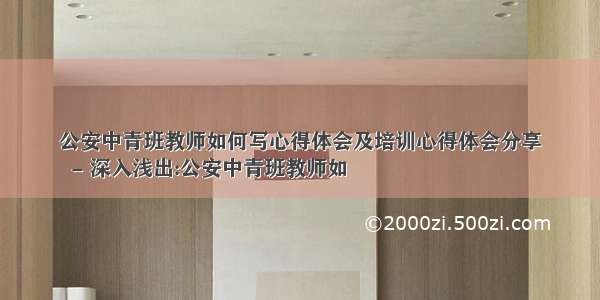文学翻译中的转译与改编都属于特殊型创造性叛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
转译
转译,又称重译,指的是借助一种外语(我们称之为媒介语)去翻译另一外语国的文学作品。这种形式的翻译,无论中外古今,都很普遍。譬如,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就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天竺文字或西域文字;英国译者诺思是根据阿米欧的法译本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语作品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卢森堡的译者,在相当长时期里是通过德译本转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们读到的英国诗人杨格的《夜思》的译本,是通过法国翻译家勒图诺尔的法译本转译的;在日本,自明治至大正初年,也大多通过英文转译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作品,有一段时期(明治代)甚至还盛行转译的风气,如森欧外,即使懂得原作语言,也一律从德文转译。
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在翻译非通用语种国家的文学作品时,因为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拥有一批通晓各种非通用语种的译者。然而文学翻译又是如此复杂,译者们在从事具有再创造性质的文学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译者本人对原作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媒介语译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滥译本,以及存在一些有独特追求的译本,例如18世纪的法译本就追求“优美的不忠”,而18世纪时法语曾是英语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有时还是波兰语与俄语之间的媒介语,通过这些“优美的不忠”的译本转译作品将会是什么结果,当是不难想见的了。
在我国,叶君健先生曾提供了好几个因转译而产生变形的例子。他把《安徒生童话》的丹麦文原作与英译本进行了对照,把但丁《神曲》片断的意大利原文与英、中译文进行对照,指出其中的巨大差异。
除了变形问题外,转译中媒介语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从五四前后直至三四十年代,日语曾经是我国文学翻译中的极主要的媒介语: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在20世纪初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就通过日语(还有德语)转译了波兰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契诃夫、安德列耶夫等人的短篇小说。之后,包括不少大作家、大诗人在内的许多小说、诗歌、剧本,仍有不少是通过日译本转译的,如高尔基的剧本《仇敌》《夜店》,雷马克的长篇小说《战后》,裴多菲的诗,等等。但是自50年代起,日语的这种媒介作用就明显地让位于英语与俄语了。这里面,政权的更迭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跟各个时代文化界人士中的留学生的由来也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从五四至40年代,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士在当时我国的文化界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从50年代起,这一比例遽减,同时出现了大批的留苏学生。
最后,转译还具体地展示了译语国对外国文学的主观选择与接受倾向。一些掌握了英语、日语的译者、作家,不去翻译英语、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却不惜转弯抹角、借助英语、日语翻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譬如巴金,在三四十年代的翻译活动中,除了偶尔翻译过一些英语作家的作品外,几乎一直致力于通过英语转译俄罗斯文学的作品。巴金晚年回忆自己50年文学生涯时这样说:“……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从这里面不难窥见中国作家,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广大中国读者对俄国文学的积极追求。
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不单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的改变,同时还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
改编经常出现在诗歌、剧本的翻译之中。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改译成文言小说《梅孽》,方重用散文体翻译乔叟用诗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朱生豪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对白(原作为无韵诗体),等等。
改编在国外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法国,纪德与巴罗合作,把德国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搬上了法国舞台,纪德也同样用散文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无韵诗体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通常,改编的“叛逆”仅在于文学作品的样式、体裁的变化上。例如,由于莎剧的中译本大多是散文体翻译的,于是中译本的读者就得到一个错觉,以为莎剧的原作也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但是改编对原作内容的传达倒是比较忠实的,尤其是严谨的翻译家,例如上述方重翻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朱生豪翻译的莎剧,因为摆脱了诗体的束缚,译作对原作的内容反倒易于表达得比较透彻和全面。当然,由于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创造性叛逆,即使是严谨的改编翻译,在作品内容的传达上照样有变形现象。
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种改编,这种改编多是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种改编严格地说不属于文学翻译的范畴,只能视作文学翻译的外延,但它对原作进行“两度变形”的性质与上述改编是一样的。
如我国着名剧作家田汉与夏衍曾分别在1936和1943年把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改编成剧本,并搬上我国话剧舞台,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改编者对托尔斯泰的原作的独特理解和改编意图,更由于两位改编者本人又是极优秀的剧作家,因此他们的改编作尽管在总的情节内容上忠于原作,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两个改编本都抹去了原作的宗教色彩”,“作品的基调、风格等显然与小说《复活》有很大的差异,它们都已中国化了。”尤其是田汉的改编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还让他们唱出“莫提起一七九五年的事,那会使铁人泪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切三的瓜,我们二千七百万同胞变成了牛马;我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话,我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样的歌,其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赫然可见。
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更多地反映在文学翻译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
作者简介
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暨翻译理论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双月刊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同时受聘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余所国内着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目前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在该校招收并指导比较翻译学专业博士生。
主要编、译、着作有:专着《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中西翻译简史》(合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越越文本 超越翻译》,个人学术散文集《海上译谭》《海上杂谈》,理论译着《比较文学引论》《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等。
本文选自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介学导论(第二版)
作者:谢天振 着
ISBN: 9787301289952
定价:52元
转自“北大外文学堂”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