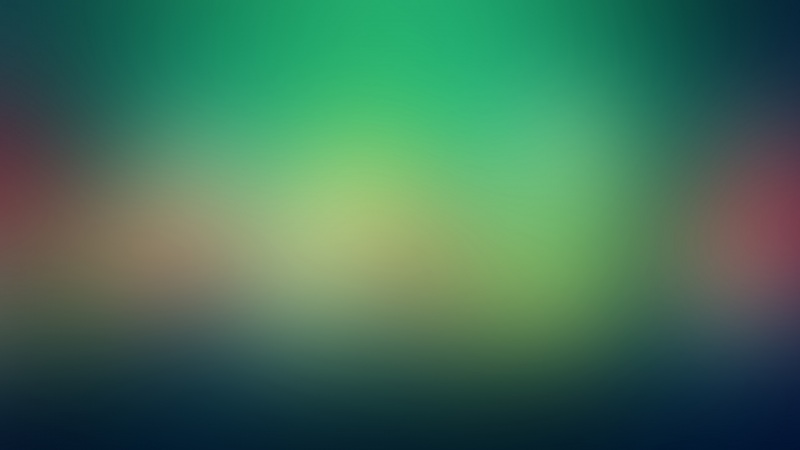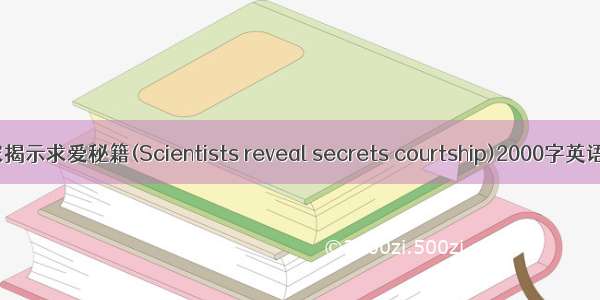“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
李存山
一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1]。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philosophy在西方为“爱智之学”,中国的“哲”字即是“智”或“大智”之义(《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希贤”出自周敦颐《通书》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将西方的“爱智”翻译为中文的“希哲”,从词组结构上说,比一个“哲”字更为合适。关键是中国古代没有“爱智”或“希哲”后面的那个“学”(学科),而且中国古人对“智”或“哲”的追求亦与西方人有差异。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学科,也就没有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2]。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绪论”中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也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3]这里首先是要立“中国哲学”之名,但金岳麟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这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4]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5]。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冯著上册是1931年出版,上下全书是1934年出版。此书对张岱年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有重要的影响。金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是张著在“序论”中所要解决的。张先生说:
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为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6]
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中国哲学问题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序论”的第三节是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这就是讲中国哲学之“异”,强调它是“中国哲学的史”。
有了哲学的“类名”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7]。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8]。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
近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界又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从认识的深浅程度来说,此问题大约有三层含义:一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二是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三是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按我的理解,最根本的是后一层含义。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哲学史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有“异”,而且有“相似点”。因为有“相似点”,所以才有“哲学”这个类名。“哲学”之名本身就与西方的philosophy有一种“连类”的关系,如果中国之“哲”与西方之“智”完全不搭界,那么就只有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带有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意味。有此意味,就不应把西方哲学当做“唯一的哲学范型”。更何况从事实上说,西方哲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的发展,为中西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相似点”,甚至“在根本态度上”也有向东方靠近的倾向,中国古代有“哲学”当是无疑义的(除非固守philosophy的“话语霸权”,或对philosophy这个学科持有成见)。
关于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我认为“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建立之日起,就是把“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以哲学名之。既然是“某种”或“某部分”,它就不是整全地研究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它是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既有消极的意义,也有积极的意义。
《庄子·天下》篇讲到先秦诸子之学从上古“道术”的分化: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中国上古时期的“道术”是学在王官、政学不分的,故它“无乎不在”(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春秋以降,学术下移、“道术”分裂,于是“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己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成玄英《庄子疏·天下》),这未免有消极的意义,但若没有这样的分化,也就没有先秦诸子,没有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孔门教法,设有四科,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四科也是一种分化,从颜渊与子游、子夏等等的高下之分,似也可看出分科的消极意义,但孔门弟子亦因有此分科而能各自发挥所长。
中国的历史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本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至荀勖的《中经新簿》才逐渐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史学从经学中分出,未免消弱了“六艺”的主宰地位,或者说,消弱了“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但史学的蔚为大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
宋明理学受佛、道二教的影响,把儒家的“性与天道”思想极大地突显出来,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取出来,这对于先秦儒学和汉唐经学实也是一种分化。明清之际的唐甄批评程朱之学“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至于宋则儒大兴而实大裂,文学为一涂,事功为一涂;有能诵法孔孟之言者别为一涂,号之曰道学”(《潜书·劝学》)。顾炎武也批评宋明理学的弊端,“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这些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无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分化,哪里会有宋以后的儒学复兴?岂不仍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清儒有“汉宋之争”,而学问大致分为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当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道术”、儒学和经学分化的背景,即它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戊戌变法之后,“废科举,兴新学”,由此开始了中国近现代的学科分化。对于这种学科分化的整体评价,已远远超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所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状况几乎可以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乱象’的一个注脚,也是促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信仰或文化信念失落的一份添加剂”[9],那么这肯定是言之过重或有偏了。胡适、蔡元培、冯友兰、金岳麟、陈寅恪、熊十力、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牟宗三等都为“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工作绝不是促成而是力挽文化信念的失落。至于现代中国学术是否可以“乱象”概括之,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克服“文化信念”的危机,这就不仅是“中国哲学”而且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合法性”问题了。
近现代的学科分化有其利亦有其弊,东西方学人倡导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是补其弊的一种方式。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问题当然比较复杂。这里又牵涉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如果中国古代既无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也无其“实质上的系统”,那么干脆就判断这个学科为“非法”。而事实是中国古代有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就是把这个系统从原有的子学、经学等等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所带来的问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既然是某“部分”,它就“不该不徧”,是有局限的;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限,是这个学科发展中的一个进步。欲弥补此局限,不是(也不可能)让“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回归那个“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而是各个学科更多地考虑彼此之间的联系(用现象学的话语说,各个学科之间有着一种彼此搭界的“晕圈”)。除了开展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之外,那种比较“整全”的中国文化(包括“大文化”和“小文化”)、思想、儒学、经学、理学、道教、佛教等等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也一直在进行。“部分与整体”的研究可以相互促进,“解释学的循环”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中国哲学”对于“整体”的研究是否构成限制或曲解的问题。如果“中国哲学”只不过是把西方哲学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搬到中国来,那么“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儒学、经学、理学等等的研究的确是构成了限制或曲解,是给它们“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外衣”。这里仍牵涉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更根本的问题是: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
三
要回答以上问题,会涉及一些学术上的争论。比如,牟宗三先生批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10]。这种批评带有牟先生自己的哲学立场,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冯先生的“三史”“六书”[11]——应该说(当然这里会有争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牟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它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2],这当然也是应该肯定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说,他所注重的方法有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关于第一点,他举例说:“如不知道中国哲学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便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不知道中国大部分哲学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则不会了解中国的人生论。”关于第三点,他强调:“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13]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大纲》,当然也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胜枚举,总的来说,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希望在更大的程度上或在更恰切的方式上表达出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的特色是什么?或它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中国哲学史界对此已有许多解答。我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应该落实到对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的继续深入探讨。
我近来有一浅见,即认为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还应回到中文“哲”字的原点,也就是“知人则哲”。此语出自《尚书·皋陶谟》,是古之“道术”尚未分裂时的一句话,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仍保留了这个“基因”。《庄子·天下》篇把古之“道术”称为“内圣外王之道”,这在《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尧典》说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讲帝尧的“内圣外王”。《皋陶谟》记述帝舜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这也是讲“内圣外王”。接下来,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是讲帝王除了正德修身之外,还要做到“知人”和“安民”。大禹说,知人则明智,能任用贤人;安民则有恩惠,人民便感怀之。在这里,“知人则哲”是古之“道术”(政学不分)的一部分,其所谓“知人”即一般所说“知人善任”的意思,还称不上是“哲学”思想。但《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智),子曰:‘知人。’”孔子所谓“爱人”、“知人”已经是古之“道术”分裂之后儒家的哲学思想,此思想与“知人则哲,能官人”有联系。且看,“樊迟未达”,孔子指点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问孔子所说“何谓也”,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孔子的指点和子夏的解说,就是“知人则哲,能官人”的意思。皋陶和大禹所说的“安民”,在孔子的思想中则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的“圣”的境界。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大禹所说“知人则哲”作“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知人善任);“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知”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论语·雍也》篇也载“樊迟问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仍是指点语。在《论语》中,“知”(智)与“仁”(及“勇”)并列,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等等。孔子所谓“仁者爱人”,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孔子说:“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与“仁”应该是统一的。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与“勇”也应该是统一的。故《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在此“三达德”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中国哲学“合知行”、“同真善”的特色。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所谓“孔子贵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贵”即最高的价值取向),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是“知人”的境界(所谓“知者不惑”),其上还有“知天命”,这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亦是为了“知人”。《中庸》又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有所不同,但通过人道的“诚之”或“思诚”(道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天人合一”。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与“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表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14])。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由“爱人”进而达到“爱物”了。
《易传·系辞上》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此话的意思与《中庸》所谓“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相仿。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虽然儒道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他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他们的共同哲学架构。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这也体现了道家的“一天人”、“同真善”的思想特点。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人间训》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报任少卿书》)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司马迁论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即是说,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是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
汉代的儒学、经学大讲“天人感应”,而主张对神怪“曼云”的扬雄也说:“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的“名教”本于道家的“自然”,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世说新语·文学篇》)宋代的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里的“学”虽然还不是“学科”之义,但宋明道学家对“哲学”的精神确实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代的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卷上)戴震的宗旨是要追究“善”为何义,但“原善”必须讲明“天人之道”,此为儒家经书中的“大训”(大义)。职此之故,我认为,儒学、经学中作为“大训”的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哲学。统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可称为“天人之学”[15]。
从“知人则哲”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之“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和人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是宗旨;就此而言,“知人则哲”可谓中国哲学的特色,“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是被这一认知和价值的取向所决定的。
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一文中引用了金岳麟先生《论道》对印度思想中的“如如”、中国思想中的“道”、古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的比较,然后指出:
中国哲学对由是而之焉的“道”的追求,使理智与情感两方面都受到了抑制,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走的是一条中间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既不像印度哲学那样完全取消天人界限,也不像希腊哲学那样使之截然二分,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所谓天人关系问题,也就是关于宇宙的本质以及人类处境本身的问题,这是世界上三大哲学系列的共性。至于这三大哲学系列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个性,关键在于它们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逻辑理路。[16]
以上论述非常重要。须知,中国哲学是取了一条不同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道”,因此,中国哲学虽然“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但知与行、天与人、真与善之间仍然是有“际”的张力的(“际”就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又须知,宇宙论(天论)、人生论(人论)以及认识方法论(知论),即所谓“三分架构”,是中、西、印哲学的普遍架构,而不是将西方哲学的架构搬到中国来;中国哲学的特色是在这“三分架构”中选择了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的“理路”,这个不同的“理路”可以说就是以“知人”为中心,以“原善”“为治”为宗旨。
在《诗经》和《尚书》中有“哲人”一词,是指“贤智”之人。孔子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把自己定位于“哲人”,然则孔子之学亦可称为“哲人之学”或“哲学”。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哲学起于贵族生活之“闲暇”和对自然万物之“惊异”[17]。与此不同的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易传·系辞下》亦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国哲学是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对社会离乱、道德沦丧的“忧患”。中西哲学之缘起的宗教、社会环境和知识主体[18]有所不同,二者对“爱智”或“希哲”的根本态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是因为“哲学”这一学科比其他学科充盈了更多的“自由”精神,所以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哲学”至今难以“定义”。瑞士学者皮亚杰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报告中,把探求“规律”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归于A组“正题法则”科学;把那些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归于B组“人文历史科学”;C组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科学”;“最后一组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即哲学学科,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但他又说:
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19]
从以上所说哲学的“己任”及其思想形态来说,中国的“天人之学”虽然在近现代经历着调整和转型,但堪当“哲学”之名是无疑义的。
近读伍晓明先生的《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其中评述了法国哲学家莱维那斯(Lěvinas)对“哲学”的看法,即:
他深刻批判了西方哲学历来将伦理问题从属于本体问题的传统,而致力于建立或者恢复伦理问题相对于本体问题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传统的价值等级应该被颠倒过来:不是伦理问题应该从属于本体问题,而是本体问题应该基于伦理问题。这就是说,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与他者的关系,才是哲学所应该关注的最根本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哲学而非本体哲学才应该是第一哲学。[20]
莱维那斯与海德格尔同出于胡塞尔之门,他也曾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二者有所不同,即他不是把“人之在世”作为“基本本体论”,而是把“与他者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道家相通,那么莱维那斯的思想则与儒家相通。这只是从哲学的“根本态度”上说,按莱维那斯对伦理哲学与本体哲学的关系的见解,中国的以“知人则哲”为特色的“天人之学”,比西方传统的哲学更堪当“哲学”之名。
在“全球化”的文化对话中,中国的以“知人则哲”为特色的“天人之学”,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普遍伦理问题、生态问题、民族问题、义利问题、身心问题等等,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 柯雄文:《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影响》注⑦,《20世纪末的文化审视》,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商务印书馆19版,第1页。
[3] 《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248-249页。
[4] 同上书,第617-618页。
[5] 同上书,第616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7]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8]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2-3页。
[9] 方朝晖:《走出学科的樊篱,回归意义的重建》,《哲学动态》第10期。
[10]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页。
[11] “三史”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为“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12]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4、7页。
[1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8-19页。
[1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5] 参见拙文《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光明日报》9月23日。
[16] 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中国哲学》第2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1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18] 余英时说:中国的“士”既重视“知识”,又有“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就其兼具两重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余著《士与中国文化》,第8页。
[19]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0] 伍晓明:《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27页。